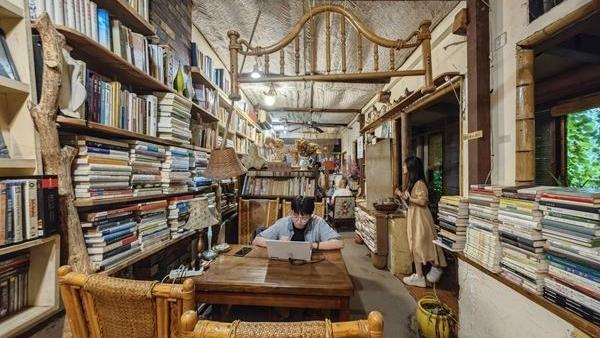【廉议汇】别让“清水衙门”沦为“腐败洼地”
多年来,“塔里木盆地找铀”始终是悬在中国铀矿人心头的未解之谜。
铀是核能发电的主要燃料,对于保障国家能源安全具有重要意义,在核医学以及农业辐照育种、食品工业保鲜、自动控制等领域,都发挥着重要作用。我国将砂岩型铀矿确定为主攻类型,主要原因在于砂岩型铀矿可实现地浸开采,资源规模大、开采成本低,且综合环保效益好,无需开挖矿石。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在北方多个盆地均取得了显著的找矿成果,但在塔里木盆地,一直未能取得找矿突破。塔里木盆地个头大、内部结构极其复杂,成矿类型有别于国内其他成功的产铀盆地。国内外都没有针对这种特殊盆地的成熟找矿模式可套用。不少业内人士认为,“沙海找铀无异于大海捞针。”
但有一个让科研人员无法放弃的理由。地质背景相似的中亚地区能形成百万吨级的铀矿宝藏,为什么一山之隔的塔里木盆地深部就不能?是不是之前用的方法不对?
中核集团首席科学家、项目负责人秦明宽带领团队梳理30年勘探数据时,敏锐捕捉到远离盆地边缘的“红层”中存在放射性异常。他大胆质疑“暗色沉积建造”和“盆缘找矿”的传统找矿思路束缚,将找矿方向转向了长久以来被视为找矿禁区的主盆区“红杂色”新层位和“盆地沙漠腹地”。“既然与塔里木邻近的中亚地区能大规模成矿,广阔的塔里木盆地深部为何不能形成铀矿体?”2020年,秦明宽力排众议,申报国家原子能机构重大科技攻关专项,组建起一支30余人的攻坚团队,其中半数为拥有博士学位的80后、90后。
沙海“长征”:青年先锋的“极限挑战”
真正的考验在广袤无垠、环境极端恶劣的塔克拉玛干沙漠腹地展开。核工业北京地质研究院铀资源探测研究部成员刘念的首次踏勘就遭遇“下马威”。越野车在千里荒漠中颠簸,窗外只有肆虐的风沙。“背着数十公斤设备和样品徒步两小时是常态。”刘念说。
更凶险的考验在次年夏季降临。当核工业北京地质研究院铀资源探测研究部成员肖菁带领小组深入天山山谷取样时,乌云瞬间吞噬晴空。“快撤!山洪要来了!”暴雨倾泻中,团队护着样品夺路狂奔。年轻师弟颤抖的声音刺破雨幕:“师姐,我还不想死,我还没结婚呢!”当最后一人扑进车厢,洪水已漫过车轮,所幸团队最终安全返回。
“我们基于智能化算法,首次构建了一套适用于巨型复合盆地和荒漠-沙漠覆盖区砂岩型铀矿找矿智能预测方法,据此预测成矿远景区10片,圈定了找矿靶区。应该说,定位的精准为我们节省了大量的时间和钻探量,即便如此,我们的实地钻探依然开展得非常不顺利。”核工业北京地质研究院铀资源探测研究部总工程师郭强回忆。
郭强最大的压力来自远景区的钻探查证优化论证。沙漠的脾气反复无常——白天,地表温度超过50摄氏度,夜晚温度却急转直下;沙尘暴袭来时,队员们只能用身体压住图纸,防止资料被风卷走;饮用水靠每周一次的车队补给,洗澡成了奢望。
深地回声:青春汗水铸就“世界之最”
随着钻探查证的不断推进,深部找矿线索逐渐显现,沙漠深部钻探查证区现场负责人刘念的神经始终高度紧绷,由于沙漠腹地几乎没有路也没有信号,驱车从沙漠边的驻地到钻探现场需要4个小时左右,为了尽可能在现场多获取一些地质信息,他索性住到钻探现场,指挥钻探部署,白天协调各项钻探施工工作,晚上整理数据,编制图件。
钻探施工方早已经忍受不了恶劣自然环境的折磨,多次提出停钻要求,现场总负责郭强顶住压力,毅然坚持:“再打30米!我签字负责!”最终测井的那个晚上,郭强和刘念都守在钻机旁边,确认了测井仪上陡然上升的曲线后,抓起卫星电话冲上沙丘,全然不顾寒风灌进衣领:“我们成功了!厚层铀矿体!”回驻地后,两人都因为受冻而发烧了。
捷报传来,背后是无数次的论证研讨甚至争执,是常人难以想象的付出。秦明宽深感欣慰:“我们不仅找到了矿,更创建了适用于全球沙漠区的砂岩铀矿探测技术体系!”这不仅刷新了世界纪录,标志着我国深地砂岩型铀资源勘查技术达到世界领先水平,填补了我国最大沙漠覆盖区的找矿空白,也为全球铀矿勘查提供了新思路。
“好多人问我,你一个博士,为什么要选择这条艰苦的路?因为,我们的梦想,就藏在这片沙漠之下,风沙再大,也挡不住我们向地球深部探索的脚步。”郭强如是说。
“每年数月的野外坚守,意味着对家人陪伴的缺失,心中常怀愧疚。然而,当自己倾注心血的研究成果最终支撑起塔里木盆地这一重大找矿突破时,让我感到更多的是成就与满足。”刘念如此回忆。
肖菁则在备忘录中写下:“我始终相信,科研就像在沙漠中寻找绿洲,只有坚持不懈,才能看到希望的曙光。感谢塔里木的风沙教会了我坚韧,教会了我如何在逆境中寻找机会,也让我们这群深爱着核地质的青年看到自身的力量。”